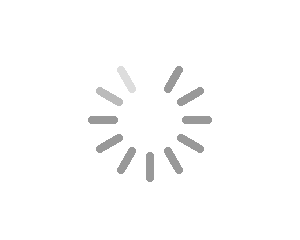来源时间为:2022-08-02
我今天要讨论的是人类群体共同面临的一个困境——育儿。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前人的尝试中得到哪些经验?分析出哪些局限?我们如何对这个状况进行探索?通过什么样的实践去解决围绕生育的种种问题?
一、为什么讨论育儿?
以往我们将生育看作是一种生物和自然性的行为,仅在生物学层面上讨论生育问题,将生育认定为是所有生物都会进行的一项行为和行动,而忽视了其实人类已经围绕生育建构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制度与社会规范。这一系列制度,包括这个制度形成的各种的文化——是否生育、谁来养育、如何培养、何为父母的标准等——对人有非常大的影响。女性主义者们发现,女性群体往往被嵌入这些制度和社会规范之中,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困境”。不同的女性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观察有着不同的答案。
二、不同女性主义者对生育困境的思考
1、18-19世纪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对生育问题的模糊态度
在我看来,18-19世纪早期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对待育儿问题的态度是模糊的。因为人们受到卢梭的影响,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可以建立道德,形成人与人的交往。女性主义者,无论是沃尔斯通克拉夫特还是穆勒,在与自由主义者的对话中,强调的都是女性也是具有理性的,可以建立道德,参与公共领域并拥有权利。她们呼吁女性走出家庭,社会也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参与到公共活动中,去拥有自己的财产,但对待生育的态度非常模糊。
自由主义女权的代表人物:沃尔斯通克拉夫特(1759-1797)
在18-19世纪中,人们认为女性要像男人一样走出去。后来的女性主义者对此提出了反思。当女性不断地走出去,超越私人领域参与到公共事务活动中,家庭内部的分工要如何解决?21世纪很多的精英女性会通过商业购买的方式,让另外一群女性去帮她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解决办法看似解决了精英女性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后者家庭中的育儿问题。
20世纪自由女性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弗里丹倡导公共领域工作女性的工作权和平等就业权。这个在今天看来得到大量支持的观点,在当时受到很多家庭主妇的反对。因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没有解决生育的问题,却一直提倡女性走出家庭走入公共领域。而家庭主妇由于在家负责生育无法走出家庭,担心自己没有价值,怕被自由主义者瞧不起,便被动员起来反对。
第二波女性主义代表:弗里丹
在此我们要注意一点,这是一些女性主义者对仅鼓励女性在公共领域从事经济政治劳动但不触及“生育问题”解决的反思,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女性主义者反对女性走出家庭,从事经济政治活动。
2、20世纪60-70年代的激进女性主义大辩论
20世纪60-70年代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中间裂变出激进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是发现女性仅仅走出去是解决不了妇女受压迫的问题,她们看到了性以及围绕性的社会性别制度加诸女性的种种困境——生育、性虐待、性暴力等,她们看到在经济之外的,围绕着性的关系形成的一个不平等的制度。
但对生育制度她们仍有争议,争议的重点在于,生育到底是一种创造力还是一种诅咒。很多人认为生育对女性来说是一种创造力,因为可以创造生命;但由于围绕生育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反而使得生育变成了枷锁。所以很多激进女性主义者会思考不婚不育这个选择。不婚不育可以作为一个个人选择,但是仍旧有大量的群体没有条件去做这样一个选择。而且在社会的延续中,生育也是很重要的一环,这时候她们就转向是否可以通过技术来解决生育的问题。
从当时到现在,技术的进步——比如人工受孕、避孕措施等——确实帮助女性解绑了生育的一部分束缚。但直到今天,技术仍然不能完全解决生育的问题,不能解决围绕着生育制度造成的对女性的捆绑。而且我们还发现,技术会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工受孕、代孕等,形成了新的阶级不平等问题。
不同于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尝试着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思考这个生育的问题。她们将生育放在一个劳动的框架下去讨论。
3、20世纪60-70年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很重要的一个贡献是继承了劳动的价值论,认为劳动支撑着整个政治经济制度的运作,并且与人类解放息息相关,劳动甚至可以形成一个新型的社会关系,一种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们由此发现了一种新的思考,那就是将生育问题作为劳动问题。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内部对此也有很多的争议,最大的争议是如何把生育看作一种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到除了公共的生产性的劳动外,还有一种生命的劳动。这种劳动在他看来是生产劳动力的劳动。在今天看来生育就是这种生产劳动力的劳动。因为人是劳动者,当一个人生育时,实际上就在生产一种劳动力。除此之外马克思还提到帮别人恢复劳动力的这种劳动也叫再生产劳动。在马克思看来,整个现代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的运作就是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支撑起来的。但是后来马克思主义把讨论的重点放在生产劳动上,忽略了再生产劳动,而20世纪60-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就把这一块拿起来重新进行讨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性劳动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创造剩余价值,支持了整个资本主义的积累。由于当时大量的家务劳动,包括生儿育女都是在私人领域里面完成的,而往往又是无酬的,所以就被认为跟资本积累无关,并且也不创造剩余价值。于是,一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得出片面的结论,认为家务劳动,包括围绕家务形成的生育问题和性别问题并不重要。
但实际上,家务劳动的价值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被资本主义的生产给掩盖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用很多方式去证明,甚至去计算家务、生育这种再生产劳动所创造剩余价值——女性在家中对家人的照料,让家人更好的工作,让孩子更好的成为资本所需要的劳动力。她们发现,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被包含在了她配偶的工作中。
正是因为这种掩盖或包含,使得很多资本主义的组织机构可以压缩给予这个家庭的工资。资本家会强调你不需要这么多钱,所以他不付给你,而实际上它在某种程度利用了女性在家中的无酬劳动。
这种掩盖的另一个副作用是它可以转移资本主义的矛盾,体现为将阶级矛盾转移为性别矛盾。比如工薪阶级里的男性在工厂里遭受种种剥削的时候,他的反应往往不是让工人们团结起来,不是跟管理者形成冲突,而是将这个矛盾转移到家中,对妻子进行家暴。于是我们发现,家庭不仅成了一个资本积累的重要基础,也成为转移劳资矛盾的重要场所。所以我们说,性别问题和阶级问题是不可还原的,很多时候性别问题和阶级问题是搅和在一起,甚至是并存的。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把生育放在再生产劳动中,放在跟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去看待的时候,跟其他的女性主义的看法不同。于是她们之间就产生讨论和对话。这种探讨不仅在性别秩序下讨论不平等与困境,更是在政治经济的视角下去看待这一问题。随着探讨的深入会发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本身也在形塑着生育相关的一系列社会安排(包括性别分工、教育体系)以及社会文化规范(生育的意识形态)。
4、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下的生育模式
到了后来,很多学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思路继续探讨下去。西尔维亚·费德里奇关于猎巫的书籍就做出了贡献并带给我们很多启发。
过去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视角下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我们会提到剥夺生产资料。当时土地是生产资料,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成为一无所有的劳动力,这是资本剥削的基础。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谈论过女性是否像男性一样通过离开土地成为劳动力。费德里奇就告诉我们,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实际上是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被锻造的。她在这本书中提到,在中世纪之前,很多女性也活动在各公共领域之中,她们参与修道院的活动,参与炼金和药草等实践,并不只是在家庭中当家庭主妇负责生育和养育的工作。而之所以这些活动被锻造成今天我们熟知的版本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它慢慢形成原始积累的过程中,需要男性成为一个可以不断被汲取的劳动力,通过攫取他的劳动力来获得资本的积累;而女性之所以要回到家里是因为资本家需要女性生育从而提供新的劳动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生育支撑起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女性的劳动就像冰山的下半部分,不可见却是基础
在中世纪或者中世纪之前,希腊时代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是组织在一起的,是围绕在家庭旁边的一种生计模式。而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人们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分开的,家庭和工厂是两个领域,劳动力要离开家庭进入工厂。于是这种“生产-再生产”的分割,可以把男性塞进生产领域,让女性待在再生产领域。所以她认为这种“生产-再生产”的模式,实际上是在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被确定下来的,并且通过我们政治和法律的形式被固定下来,成为一种社会规范去影响人们的观念,让人们在出生以后就接受这种观念,习得这种规范,然后再不断去再生产这种模式。
费德里奇提到,当时有很多女性去挑战这种模式,但她们会被贴上巫女的标签受到惩罚或猎杀。通过她的启发,我们可以打破一些迷信,从而意识到性别分工、生育制度、建立在生育制度上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其政治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且它不是不可变的,它是可变的,并且可再建构的。
《卡列班与女巫》书影
5、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生育模式转变
南希·弗雷泽对资本主义不同发展时期的“生产-再生产”的模式进行了分析。比如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形成了男性成为养家者,女性负责生育这样的模式。后来随着这个过程的发展,它会出现各种矛盾,比如生产领域会出现生产过剩,出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生产领域产生的矛盾也会波及再生产这个领域。许多社会学家做过相关的研究,研究工人家庭内部的种种问题,比如家庭的破裂、孩子的教育,人作为劳动力的枯竭,还有贫穷等种种问题。
资本主义是可以自我调试的。所以在这样的矛盾中,资本主义的国家开始把工人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拿出来作为福利,体现为使用公共福利(比如公共的育儿机构)或者家庭津贴去承担一部分生育责任,从而解放女性劳动力。一方面它可以让这些女性劳动力从事更多的生产,创造更多的价值;另一方面,它也把所有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中的一部分,通过分配的形式去承担一系列生育的负担。最明显的就是福利国家会给工薪阶层的家庭,甚至是单独给女性一些津贴,用于女性再生产劳动。
但是1990年代以后,很多国家采取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当金融资本进来以后,很多通过分配方式提供的福利又逐渐撤回。资本鼓励更多女性参与生产,通过生产获得薪资再去购买服务,而购买的服务是另外一部分(工薪阶层的)女性解决的。在1990年代,很多情况是第一世界国家的女性让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来从事服务,第三世界的国家比如菲律宾和很多亚洲国家的女性,就得离开她们自己的家庭去为第一世界的女性服务。但我们会发现,这种方式只是把生育问题转移了,再生产的危机仍然存在。
三、对思考中国的“生育问题”有什么启发?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看到了生育背后的政治经济的转型,看到它跟整个市场资本,甚至是政治之间的关系,那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的问题有什么启发?
我这几年一方面在阅读在思考,另一方面在关注各种实践,试图去寻找这个答案。但是几百年来,人类都在思考这个难题,它不是我们通过想象力就可以解决的。重要的是要通过大家共同的探索,甚至是很多的社会实验,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反思,才可能去探索一点点推进。
我在这里也一点点我自己的一些的思考和探索。生育问题是人类普遍的一个问题,这个改变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的。刚才讲到的西方的这些讨论对我们的启发就是,我们会发现生育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困境,不仅是女性群体的困境,也是整个国家的,不同阶层里的共同难题。重要的不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围绕着生育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因为个人所面临的困境也是整个社会危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