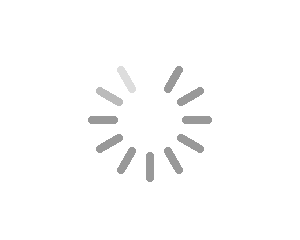侯淑侠是当年大队文艺宣传队的四大花旦之一,也被请来了。敬民书记递给我一张黑白照片——四十年前,四个女人在田头演节目时拍下的——指着照片中的一个说:“这个就是侯大娘。”
侯大娘说:“这几个人中我最年轻。哎,我今年也快八十了。最大的那个已经不在了。另外两个也有九十了。都老了!”说起当年的文艺宣传队,老人一脸兴奋,说“经常去县里演出,都是坐拖拉机去。只要有来参观的,放下农活就演。她们几个都不识字,我还识几个字,不光能唱能跳,我还能编节目,表扬啥了,批评啥了,我都能给他编成节目,然后就排练,田头地边就演了。那会儿……真是,觉得才好,才有心劲儿!多少年都没这样的事儿了。支书跟我说,想再组织演节目,你看,我都快八十了,还弄这干啥,有年轻人,叫他们演。我怕不行。”
支书说:“咋不行,你得把当年的劲儿拿出来,也给年轻人做个榜样。行,你一准行。”
“你支书说行,我就试试?想想那会儿,咱村的节目都演到县里,一有演出,都是坐拖拉机去……”
几天后,我又去了朱楼。车子还没进村,就听到了乐声。乐声是从支书的院子里传出的。
朱楼是个经济薄弱村,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两委开会,或者商量啥事儿,都在支书家里。演出前的一些准备工作,都是在支书家里进行的。
我到的时候,敬民书记正埋头调音响。对于朱楼来说,这套音响太现代了,包括支书在内,谁也没摆治过这种“高科技”。目前能摆治它的,也就是敬民书记了。操作台上的灯光一闪一闪,乐声也时高时低。旁边站着两个七八岁的小孩儿,不声不响,眼睛不离操作台,台上的灯闪闪发亮,孩子的眼也闪闪发亮。支书叼着烟,盯着敬民书记的手,自己的手却插在裤兜里。还有个年轻人,双手抱着膀子,嘴里也叼着烟。一个穿大红羽绒袄的年轻女人,把话筒凑到嘴边,喂喂两声,又拿手拍拍话筒,再喂喂两声。还有几个人,站得虽然远些,但注意力也都在这台“现代化”上。
支书看到了我,迎上来握手,并指着两位年纪大的介绍说:“这是张老师,这是谭老师。”
谭老师是张老师的学生,说打小跟张老师念书,一直念到1976年,然后就在村里教书,一直教到现在。我就跟他聊学校的事。他说村小学现有5个班,一个年级一个班,没有六年级。大概看我是“县里来的”,就说:“现在的政策好了,农村教育经费有了保障,国家按每个学生700元拨款给县财政,财政再拨给镇中心校。咱这基本没有失学的,除了个别智力有点问题,自己又不愿上学的孩子,该入学的都能正常入学。学费也是全免的。”谈到留守儿童,他说,“留守儿童也有,大约占四分之一,都是跟爷爷奶奶生活,每天由爷爷奶奶接送上学下学,孩子的父母年年都回来……”
张老师说:“我教了一辈子书,村里五十多岁的——包括咱支书——几乎都是我的学生。我今年67岁,打小就喜欢文艺,尤其喜欢拉二胡。我热文艺,是受父亲的影响。他喜欢豫剧,哪里有戏,他就跑去听。他也会唱,唱得还才好。那时候,咱村的文艺是最有名的。那一年,县里搞巡回演出,挑了两个宣传队,其中就有咱村的。群众文艺太重要了!能拉近人与人的距离,融洽村民之间的关系,也能教人学好向善。有啥不愉快的,说说唱唱,蹦蹦跳跳,就把不愉快给忘了。谁跟谁有点儿言差语错的,一同登台,搭档演出,然后也就没事儿了。现在,不缺吃不缺喝,就缺个心情好。心情好了啥都好了,生活有信心,干活也有劲儿。六七十年代,活动搞得多好!这几年时兴广场舞,很多人热这个。但光这个也不行,不能都跳广场舞吧。今年搞这个(文艺演出),我看是最好了!支书太有眼光了,他支持,他不光口头支持,还自己往外掏钱。上级给咱派来了第一书记敬民同志,那是太好了!虽说他是上面派来的,但咱没把他当外人儿。他也踏实,又年轻、肯干,能走到群众中间,能为老百姓办事儿,来到第一件事,给村里安了路灯,咱村子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以前哪有路灯,是他来了才有的。老百姓对他都是欢迎的,赞成的。”
支书说:“张老师是咱的艺术指导,他和谭老师都是文艺骨干。原来我还担心搞不起来,虽然咱村过去文艺搞得不错,但多少年都不弄了,谁知能不能弄起来。现在都热抓钱儿,谁还有心思弄这些。真没想到,群众的热情还是这么高,一说报名都报名,不让谁演谁都不愿意。”
张老师说:“六七十年代,俺父亲和金玉书记一样,都喜欢唱戏。那会儿,可红火了!上头也高兴,群众也满意。后来就断了。现在,咱韩支书还跟当年的金玉支书一样,也热文艺,支持文艺。他一说要搞演出,人就聚来了,你看今天来多少人,都欢迎这个。那边舞台也搭好了,都攒着劲儿,就等着登台了。”
支书马上接着说:“搭这个舞台可不容易。村里没收入,两手拍啪,啥也没有。把我家的楼板儿拉过去。还有砖,也拉过去。还得买白灰、买砂子、买水泥,这几样,我就花了2000多块。又花钱请了5个工人,总算是弄好了。工人走了,我去一看,觉不行,这么冷的天,刚抹的水泥,那不冻坏了?拉了草苫子盖上,才算放心。我弄这个,家属开始不理解,昨晚叨叨我半小时,说我当的是赔钱的支书。其实,她就是嘴上说说,叨叨完了,啥事儿没有,跳舞去了。嘴上说我埋怨我,但她也没挡着我,我拉去的楼板她也没给拉回来,我盖上的苫子她也没给拽下来。这也就算理解了。妇女家,也就是个嘴。”
支书说着,掏烟让了一圈儿,有接的,有说不会的,他就自己点上,抽一口,然后把烟卷儿放在手里捻,边捻边说:“我弄这个,不光家属不理解,群众也有不理解的,说支书你弄这些有啥用?他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就是啊,弄这些究竟有啥意义。但是细想想,还是有意义的。现在的人啊,都变了!出去打了几天工,回来就嫌弃农村了,说农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总跟人家城市比。咱就是个农村人儿,你就过你的农村日子,跟人家城市比啥?没想想你是咋长这么大的。农村把你养这么大,你出去转了一圈儿,长了本事了,回来就嫌弃农村了。还有些村民,闲着没事,张家长、李家短,说三道四挑是非、扯老婆舌头,这不都是闲的!”
我笑着插一句:“能在一起扯,说明村民之间还是有交往的。城里人可不扯,住在一个楼里,三五年互相不认识,这倒没有老婆舌头扯,但人情味儿也没有了。”
支书没接我这个腔,仍然按自己思路说:
我年轻的时候,有回路上遇着下雨——我穿着皮衣,有点儿雨也不怕——有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拄着根拐棍儿,走走停停。我下车问她上哪去。她说去李楼。李楼还有一大段路,这么大年纪,颠着个小脚,雨还下着。我说你上我的自行车,我送你回家。
那会儿,遇到老年人,你敢骑车子驮她回家。现在你敢?
还有一回,俺家属拉车运草,也是遇见个老人,小脚,走路颤颤巍巍。家属说,你这样啥时能到家?上车吧,我送你回家。到了家,老人也是感激,跟俺家属说:谢谢神!谢谢主!弄得她哭笑不得,说,你看,你看,我费劲巴拉地送你回家,你不说谢谢我,你谢谢神,谢谢主,是神送你来的,还是主送你来的?说起来都是笑话。
现在,农村变了。你比如,过去谁家婆媳不和,或者兄弟纠纷啥的,谁都能上去劝说劝说。本来就没啥大矛盾,有人打个圆场,给个台阶,该赔礼赔礼,该给面子给面子,事儿就了了。现在呢,遇见谁家有搿气、打架的,要么躲着装作看不见,要么站一旁歪头看热闹。谁也不劝说,都当看小品。这是为啥?社会变了!不是变好了,是变坏了!啥原因?素质!素质啥原因?教育!咋教育?光讲大道理?上面号召搞群众文化,这个好!广场舞,村村都搞,镇里比赛,县里比赛。就说咱村吧,也是天天晚上跳。咱村条件差,场地也没有。我家门口是大路,还算平坦点,就在那儿跳。广场舞好是好,不能都跳广场舞吧。比如年纪大的,想跳也跳不起来了。俺就商量着,得把咱的传统拾掇起来,搞多样化的文体活动。这不,舞台咱也建了,等水泥干了能站住人儿了,咱先演一场。过年正月十五再演一场。舞台咱也不拆,啥时想搞就搞它一场。每周一次行不行?不行就每月一次。图个高兴嘛。人家都过得开开心心,咱为啥不能也开开心心?再说,文艺活动也是一种教育形式,有了好的事情,编个节目一演,就都知道了。有了不好的事情,比如,乱倒垃圾的,不孝顺爹娘的,扯老婆舌头的,咱就编个节目上台演,也算是对这种现象的批评。时间长了,素质也能提高点儿,你说是不?
咱村是个贫困村,一分钱没有,多亏敬民同志,从县里给咱争取一套音响。这套音响高级了,镇里都没有。村民也有想唱歌的,但村里没条件,只能到镇上花钱唱,一块钱一首,过过瘾就得好几块。还不光是钱的事儿,主要是不方便,得跑十几里路,等跑到地方,也累得不想唱了。现在音响有了,还得需要钱。你得耗电吧,不光音响本身耗电,灯光也耗电。村里没有集体经济,别说这个钱,新安的路灯,电费都是从干部身上出的。你有给村民办事儿的心,没钱你也办不成。这套音响的电费,也是没有出处。咋办?我先掏呗。原来也想搞光伏,这个还真好,不光解决了自己的用电问题,电发多了还能卖钱。事儿虽然是好,结果也没弄成。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没有钱啥事儿你都不好办。再说往学校去的那个桥,前儿下雨,把桥冲断了。还算好,往上跑了几趟,“小公基”项目给了点钱,总算把桥修好了。那个桥,我一直担着心,老怕出事儿。有一回,机动三轮把桥轧塌了,车也翻沟里了,幸好没伤着人。今年夏天那场雨,我打着伞,在桥头站了两个多小时。送孩子上学的三轮车,都打桥上过,骑得又快,泥路又窄又滑,水有两米多深,还是个急转弯儿,孩子坐在车里,滑到沟里就不得了!哪家的孩子都是宝贝疙瘩,出了事儿咋办?我站在那里,跟个交警似的,谁来我就叫他下来推着走。
扯得有点儿远了。还是说咱的文艺演出吧。村里成立了文艺演出队,我当队长。还打算给文艺骨干发证书。这样朝外一公布,报名的多了!选了一部分,排了几个节目。有婆媳同台演出的小品《婆媳情》。婆婆也是金玉书记那会儿的文艺骨干。
腊月二十四,天气晴好。
村里热闹起来,南北大道的两端,还有自西而来的水泥小路,三个方向的人车都往这里赶。多是电三轮,也有两轮电车,也有四轮私家车。三轮多由女人驾驶,车上坐着孩子或老人。更小的孩子,或被车上的老人抱着,或由开车的女人亲自抱着。一手掌住车把,一手揽孩子在怀里。孩子也很合作,一点儿也没影响车的速度。还有很多提着矮板凳、扛着长条凳,走着过来的。
舞台在村卫生所大院儿里,门外横七竖八停着各色车辆,院内院外的人跟庙会一样多。一根长绳从大院上空穿过,绳上拴着许多红灯笼,几条彩带在风中舞着,四周的墙上也都插着彩旗。
敬民书记专注地操作着音响,随着操作台上的灯光闪烁,声音也时大时小地变换。突然,一声啸叫,惊得人们转身后躲,几个孩子连忙捂住耳朵,抱小孩儿的女人,赶紧把孩子的头脸拿手遮住。
第一书记敬民,既是策划和导演,又是演出的音响师。演员队长是支部书记,他负责演员的组织。两委其他成员则散开来维持秩序。
支书悄悄跟我说:“几十年没有这样的场面了。但我有点儿担心,几百人在这里,万一……安全是我最担心的。”
观众大都自带板凳,没带板凳的就在外围站着。一些孩子坐不住,在人堆里钻来钻去。
我们被邀在第二排就座。中间几只木方凳,两旁是些矮小的凳子。前面一排是孩子的座位。刚坐下,后面就有人说:“挡住了,挡住了。”我有点儿坐不住,但也不好起身就走,毕竟是村干部的盛情。方凳横放了,是比刚才矮了些,还是会挡后面的视线。虽然后面不再抗议,但我还是觉得不安。熬了几分钟,说了声“出去拍几张照片”,便起身绕到了人群外面去了。
两个多小时,十几个节目:声乐、器乐、戏曲、小品、快板和舞蹈。下自七八岁孩童,上至八十岁的老人依次登台。琴声、鼓声、唢呐声,歌声、笑声、掌声、欢呼声,一阵又一阵。演员下台又成了观众,观众上了台就是演员。计划内的节